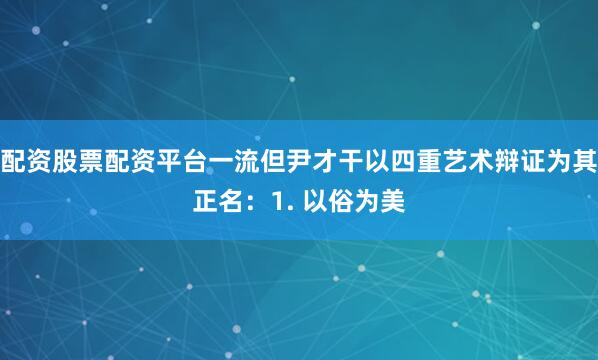
俗韵雅心最相宜——论尹才干《赞平民打油诗》的平民诗学与时代意蕴
/
赞平民打油诗
◎尹才干
/
平民小贩张打油,出口成诗味道馊。
酸甜苦辣滋味美,嬉笑怒骂上心头。
/
尹才干的《赞平民打油诗》以四句凝练之语,为“打油诗”这一长期游离于正统诗坛边缘的文体正名。全诗以“张打油”为符号,串联起平民生活的酸甜苦辣与嬉笑怒骂,既是对打油诗本质的精准概括,亦是对其文化价值的深情礼赞。以下从历史溯源、艺术特质、社会功能三方面展开评析。
一、历史基因:从张打油到“才干体”的平民诗脉
打油诗之名,源自唐代南阳人张打油。其《咏雪》一诗: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,以俚俗之语勾勒雪景,无“雪”字而雪意盎然,开创了“不拘平仄、直白诙谐”的诗歌传统。尹才干诗中“平民小贩张打油”一语,正是对这一源流的致敬,对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。
展开剩余75%历史上,打油诗始终承载平民智慧。比如“天高不算高,人心第一高。井水做酒卖,还道无酒糟。”(《王婆酿酒》),这首打油诗告诫人们要知足,否则就会成为“贪欲”的奴隶,并受其害。
也反映文人雅士的俗趣,如苏轼以“竹笋焖猪肉”戏谑雅俗之辩(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”);鲁迅以《南京民谣》“大家去谒陵,强盗装正经”讽刺政客虚伪。
尹才干提出的“才干体打油诗”,正是这一传统的现代表达—在顺口溜中注入“新声韵”与“文采”,将田间地头的“味道馊”升华为“滋味美”。
二、艺术特质:俗中见雅的语言张力
打油诗常被误读为“技术含量低”的“文字虫卵”(尹才干语),但尹才干以四重艺术辩证为其正名:
1. 以俗为美,反叛形式枷锁
“出口成诗味道馊”中“馊”字看似贬义,实指打破精致诗语的陈腐框架。如张打油笔下“白狗身上肿”的笨拙意象,以生活化比喻解构雪景的典雅范式,反得“画龙点睛之妙”。
2.嬉笑怒骂,淬炼情感烈度
“酸甜苦辣滋味美”揭示打油诗的情感容量:胡适《兰花草》以“一日望三回”写盼花之切;金岳霖剃发后自嘲“此头千载光溜溜”,皆以诙谐包裹人生况味。
3. 韵律自由,激活语言生机
打油诗不囿于平仄,却自有节奏。如尹才干《武胜歌谣》:“四条小河一座山,一根玉带绕中间”,以民歌式复沓营造地域风情,把武胜“一江四河一山”的地域形态描绘得惟妙惟肖,诗意盎然,一听难忘,证明“俗韵”亦可承载诗意。
三、社会镜像:平民话语的文化赋权
打油诗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平民性——它既是“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百姓之诗”,也是“文人回归世俗生活的精神通道”。
为边缘者立言:如尹才干写市井小贩的艰辛,“街边小摊卖冰棍,天没亮来抢摊位。希望早点来卖完,回到家里补瞌睡。”为农夫期盼插秧雨写的,“春雨贵如油,何时田里流;把秧插在云朵上,秋来丰收不用愁。”
解构权力话语:鲁迅以“静默十分钟,各自想拳经”撕破政客伪装。
重建文化认同:尹才干《故乡》等作品以方言俗语书写乡土记忆,使“打油诗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言者”。
正如学者王珂所言,打油诗是“正统诗体的俗化形式与非正统诗体的雅化形式”,它在雅俗裂隙中开辟了属于平民的诗意空间。
四、尹才干的创新:打油诗的当代转型
作为“才干体打油诗”创始人,尹才干对打油诗的革新体现于两点:
1.形式实验:将打油诗与十六行体融合,如《夜宿武胜》以五言句式重构田园意境,在自由中植入节奏感。
2.主题升维:其《缝补岁月》等诗作,将“捏酒杯的手”“午夜祈祷声”等生活碎片,升华为对时光流逝的哲思,证明打油诗亦可承载存在之重。
结语:何以“滋味美”?—平民诗学的永恒价值
尹才干的《赞平民打油诗》,恰如为千年打油传统题写的墓志铭:它以“嬉笑怒骂上心头”的率真,对抗虚伪矫饰;以“酸甜苦辣滋味美”的包容,拥抱人间烟火。当我们在AI写诗、后现代解构的喧嚣中迷失时,或许更需重拾张打油井边的黄狗、胡适盆中的兰草——那些扎根泥土的“俗韵”,终将沉淀为文明最发达、最坚韧的庞大根系。
诗根在野莫嫌俗,打油三寸有天地。打油诗之“馊”,是市井烟火的气息;其“美”,是一碗烟火、四方食事、百味人生、万种风情,是生命本真的力量。它从不需登大雅之堂,因为它的殿堂,就在每一处飘着炊烟的人间屋檐下。(元宝+佚名整理)
发布于:四川省正好配资-配资杠杆之家-配资炒股网股票-配资实盘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